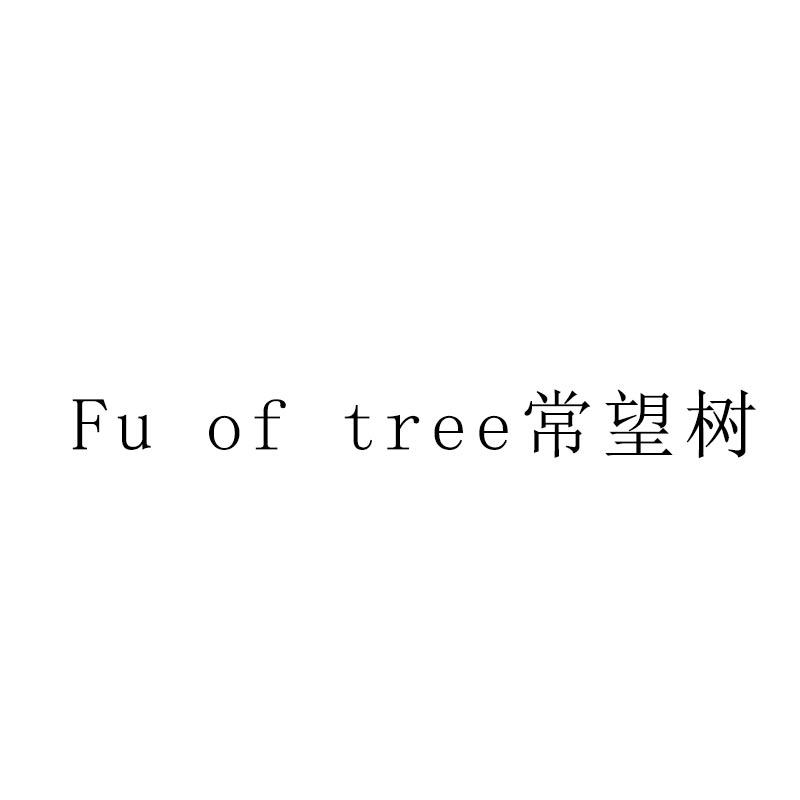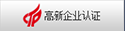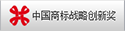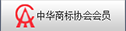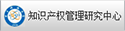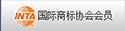原棉价格涨三倍 山东棉产区产量少难抵极寒
尽管“千年极寒”的说法引来争议一片,但纺织品价格蹦高却是不争的事实。从内衣鞋袜到秋冬服饰,从被褥床单到沙发窗帘,一种“疯涨病”开始在所有与“纺织”这两字有关联的领域中蔓延。逐渐地,追根溯源的眼光盯上了棉产区,似乎那里隐藏着这场“群体涨价症候群”的罪魁祸首。
山东棉产区产量下降 难抵棉业极寒的确,籽棉收购价格已从去年的每斤不到2元,一路涨到了现在的每斤6.2元,甚至更高;皮棉价格也从去年每吨1万元的便宜货,摇身变成了每吨25000元的紧俏物资,但是当记者连日探访省内多处主要棉产区后发现,本轮涨价的真正源动力似乎藏在更深处……虽然“上青天”的光环早已暗淡,但纺织产业无疑仍是青岛产业结构中的重要一环,近800家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加上无数的中小型纺织企业,每年创造着以百亿计算的产业价值。然而今年的寒风却过早地吹袭着青岛的纺织行业,首先出现不良反应的,是中小型企业,紧接着大型棉纺厂也出现了“重感冒”。
“箱底货”卖得比新款火10月19日,记者走进市南区爱购广场时,这里已经是“寒意袭人”了,与去年同期相比较,今年新款秋冬季服装出现了集体性涨价,而且上涨幅度也大得惊人。
“以前10月份是秋装卖得最好的时候,今年的销量明显不如去年。”在爱购专营休闲服饰的崔小姐告诉记者,今年她所代理的千依、世林等几款服装品牌都出现了涨价的情况,而且涨幅都接近了20%,如此巨大的涨幅,不光是消费者无法接受,就连她本人也很难接受,“现在物价一直在涨,要是涨得少点,大家还觉不出什么来,可涨得这么多,消费者就不买账了。”其实崔小姐也是一肚子苦水,这次涨价并非是代理商或个别品牌的偶然行为,而是由原材料引起的行业性调价,其幅度与规模在服装行业中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。对此,爱购广场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,今年的秋冬季服装涨价主要还是厂家提价,商家随之水涨船高,而且规模不仅局限于个别品牌或种类,“现在不少商家甚至拿出一些旧款的秋冬季服装来卖,而且销售情况还不错,就是因为今年的秋冬装进价太高了,就算是要卖,零售商也不得不摊薄利润。”
这场“千年极寒”的影响远不止于此,服装行业也并非受影响最为严重的领域,跟棉花挂钩更为密切的家纺行业情况更让人担忧。在水清沟的一家床上用品加工店,一幅宽1.5米长2米的单层大红床单,现在的包料加工价格已经涨到了150元。“你要是觉得贵,就自己买料子来做,我保证我的手工费跟去年相比,一点也没有涨。”店老板邓先生告诉记者,这幅大红床单所用的布料,今年的售价已经达到了每米35元,而去年一模一样的布料每米只要16元。正是因为布料的翻番涨价,使得邓老板的生意难做了许多,“我现在一般不接包料的活儿,一方面是价格太高让人觉得我黑,另一方面是,不想把手头的存料用完了。”邓老板说,现在的布料已经不是一天一个价了,甚至上下午就会变一变,他并不想在这个时候进料,生怕进贵了砸在手里。
中小型服装厂遭遇“布寒”
正是因为布料的涨价,青岛森山服饰公司的崔宪哲不得不减少了产量。作为设在城阳区的一家小型服装加工厂,崔宪哲前几年刚刚从纯粹外贸加工型企业,转型为内销型服装企业,也拥有了自己的服装品牌。对于今年的布料涨价,崔宪哲表示,比2008年的经济危机还让他感到恐怖。“2008年经济危机虽然说不景气,但我的厂子始终没有停顿生产,接到的国外订单是少了,但做一单就赚一单的钱,可今年我是做一单赔一单。”崔宪哲告诉记者,青岛地区的中小型服装加工企业,主要还是依靠南方布料的支持,本地生产的成品布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,因此对于原材料的定价毫无发言权,只能逆来顺受。“今年的布料价格涨得太吓人了,很多加工厂已经不开发新款,而是拿库存的布料继续生产去年的旧款服装维持,有的干脆让工人轮班生产,更严重的甚至停产歇业。”崔宪哲说,对于原料涨价,服装加工厂承担了缓冲带的作用,因此所承受的价格压力,远大于零售终端,日子更不好过。
青岛拥有多家大型棉纺厂,可以生产大批量的坯布,但成品布加工能力则相形见绌,对于这个产业链断点,城阳区一家中型服装加工厂的负责人苟经理深有感触,因为成品布的过度涨价,他的厂目前仅接受零散订单,对于动辄需要上百吨成品布的大订单,他现在只能有心无力。“很早以前,青岛纺织业走的是纺印染整体发展的路子,可现在印染已经成为了青岛纺织行业的弱项。”苟经理表示,现在青岛几家大型棉纺厂所生产的坯布,基本都是出口或远销外地,被加工成品布后再以数倍于坯布的价格卖回青岛,更产生了巨大的物流内耗,对于青岛的纺织业发展是个短板,“现在我的成品布主要来自于南方,像江苏南通这样的城市,它们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整个中国的布匹流通。”
而对于曾经涉足的家纺行业,苟经理表示,现在就是借他个胆也不敢接触了,“跟棉花的涨价相比,成品布的涨价就更是小巫见大巫了。”
#p#副标题#e#
小型家纺厂只剩“底牌”
10月19日,青岛正一家纺厂的仓库里,只剩下1.2吨棉花了,它们是这家小型家纺厂最后一张“底牌”。“现在我基本不敢开工,要是把最后这点棉花用掉了,正一也就走到头了。”该厂负责人王先生告诉记者,自己跟棉花打了一辈子交道,也没有想到棉花会涨到今天这个地步。
早些年曾在青岛某国棉大厂担任领导工作的王先生,对于青岛的纺织业发展可谓是了如指掌。“以前都是销棉的求买棉的,现在倒过来了。”王先生回忆说,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,山东还是全国的主要棉花产区之一,从胶州、平度到高密、淄博,从滨州到东营、菏泽,到处都能见到白花花的棉田,可随着农村产业结构发生变化,棉花价格的持续疲软,山东各地区的种棉面积被经济作物、工业园、住宅楼、开发区一点点蚕食着,平度、高密这两个当年的产棉大县,如今一块棉田也见不到了。尽管如此,纺织行业也从未出现今年这样的“棉荒”现象,棉花的价格也保持着相对的稳定状态。
最初的价格地震出现在2008年,受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,当年棉花价格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滑坡,籽棉收购价格跌至了每斤1元钱,严重挫伤了棉农的积极性,这也给两年后的“棉荒”埋下了祸根。“去年的时候,我跟几个固定的棉花供应商是一个月定一次价,后来变成了一个周定一次价,现在干脆是上午一个电话、下午一个电话。”王先生告诉记者,多亏他凭着多年磨练出来的行业敏感,在今年棉价还没上涨的时候提前购进了100吨棉花,正一家纺厂才能维持到现在,可这点“家底子”也逐渐用光了,“如果棉花价格再不回落,我只好走出最后一招了。”王先生告诉记者,与服装业不同,家纺业受棉花的影响更为直接,因此承担的价格压力更大,大规模的厂子还能顶住,小厂的抗风险能力太弱,顶不了多长时间。
大型棉纺厂大半用“外棉”
正如王先生所说,岛城个别大型棉纺厂情况并没有外界想象得那么惨淡,但同样面临着突出重围的考验。
10月19日,记者来到青岛一家大型棉纺厂采访,远远就听到车间内传出隆隆的纺车轰鸣声。走进该厂的前纺车间,里面是一片繁忙景象,一捆捆的棉花在这里先是被梳成棉绺,然后编织成棉纱,再重复两股并一股的魔术,最终产品就是一轴轴的白色坯布。
“今年棉花涨价对我们有影响,但我们相信能顶过去。”该厂贸易事业部的顾主任告诉记者,目前厂里的棉花库存量确实有些吃紧,但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的正常运营,但对于具体库存量顾主任表示,属于商业机密不便透露。但从生产各环节的蛛丝马迹,还是能看出“棉荒”对于这家大型棉纺厂的严重影响。在前纺的一个车间,记者看到两台大型机械正在将一垛垛的皮棉打散,并进行初步处理,但是同一车间的另外两台机械处于停工状态,而在纺纱车间,记者看到了同样的现象,有近一半的自动纺纱机没有开动。
在一间处理废棉的小屋里,记者看到一摞摞从皮棉里梳理出来的棉籽和杂质,这里的一名工人告诉记者,以前这样的废棉就被农民拉去沤肥了,现在有很多小厂争着来收这些废棉,拉回去再加工一下用来填被填枕头。而每一个车间,记者都看到有女工负责打扫地面的棉絮,然后集中存放起来。除此之外,在一个加工车间内,记者还看到了一份考核表,上面清晰地列出了各工序的节约标准,严格控制着整个流程中对棉花的浪费。
光“节流”不够,更重要的是开源。该厂的一名崔姓工程师告诉记者,现在厂内使用的棉花一大半依靠进口,主要是来自美国及加拿大的“外棉”,而省内的棉花非常少。青岛海关的统计数字,也侧面印证了外棉对于这些大型棉纺厂的重要性。根据统计,单纯今年前7个月,山东口岸就进口棉花73.9万吨,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65.1%;进口平均价格为每吨1776美元,上涨39%。一定程度上说,如果没有地处口岸城市的优势,缺乏“外援”大型棉纺厂也将面临无米下炊的困境。
#p#副标题#e#
棉花发“疯”病根在哪?
都是棉花惹的祸!一切的线索都指向了纺织行业的根本——棉产区。为了一探纺织行业“疯涨病”的究竟,记者先后探访了省内的高青、博兴、邹平等多处棉产区,答案却远非记者所预想的那样。
世间没有“无因之果”,只是这原因藏得太深……■第一站:滨州市店子镇 收购站一大半“饿”着滨州市店子镇,很早就听说这里是鲁北最大的棉花收购加工基地,寻找“金棉花”的第一站自然而然地定在了这里,但这里的萧条景象让记者大吃一惊。
记者从淄博市驱车1小时便进入了滨州市店子镇的辖区,但在店子镇开了足足20分钟,一片棉田也没有看到,如果不是路旁鳞次栉比的“棉花收购”招牌,还真难相信这里曾经是有名的棉花之乡。而这一个个棉花收购点,也显出一片萧条景象:紧锁的大门、空荡荡的晒场和慵懒的看门狗。
拜访了三四家收购站,记者得到的答复都是“没有棉花”,就在快要丧失信心的时候,终于看到了一大堆棉花!在店子镇张王村的万达油棉公司兴发分公司,负责人魏先生告诉记者,他是附近十几个收购站里惟一还有棉花的收购点。在这家收购点的广场上,晾晒着约200吨的籽棉,但对于这点成绩,魏先生感到不值一提。“去年我最多的时候一天就收500吨籽棉,你算算这是个什么概念。”魏先生说,今年的棉花不光是价格涨得厉害,收购起来也很困难,整个店子镇的百余个棉花收购点里,目前能像他这样还维持正常运作的不足40个,“现在的收购价已经是每斤6.1元,我干了这么多年棉花生意,从没见过这么高的价!”
籽棉在这些加工厂经过粗加工,打包成皮棉然后外销,“这200吨籽棉是发给滨州的,现在棉价这么高,我们这些棉贩子根本不敢存,怕砸在手里。”魏先生驳斥了记者关于棉贩囤棉的猜测。对于棉价的异常上涨,魏先生归因于“天灾”,“今年雨水太大了,对棉花的产量和质量影响都不小。”
来到店子镇政府驻地,那曾经年产皮棉20万吨的80多家棉花加工企业早已荡然无存,取而代之的是“优质西红柿之乡”的巨大标语牌。
■第二站:淄博市高青县 棉农抱怨收入不增反降“到高青去吧,那里有棉花。”因为这句话,记者转至淄博市高青县,在这个全国产棉百强县,记者如愿以偿看到了大片大片的棉花田,还有辛勤憨厚的棉农朱兴亮。
朱兴亮是高青县李凤鸣村的一名村民,家中的10亩地种的都是棉花,他一边采摘棉花一边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“棉花涨价跟我们没关系,该赔钱还是赔钱,只不过少赔点就是了。”朱兴亮说,他今年的心情是三起三落,春天的时候,看着长势喜人的棉花别提多高兴;可紧接着8月份的连续20多个连阴天,让他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;到9月份,籽棉收购价蹭蹭上涨,他又是一喜;可接下来摘棉的人工费暴涨,又让他无奈。
“往年每亩棉花产量在600斤左右,今年‘结桃’的时候雨水太大,亩产量也就400斤。”朱兴亮说,尽管如此,因为棉花价格翻着番涨,他还是能赚个盆满瓢溢的,可采摘人工今年也跟着翻番了:往年都是论天算钱,一个人一天四五十元钱;今年成了论斤算钱,一斤就要1.2元到1.4元,一天下来雇一个人就要120元左右。即便这样,朱兴亮也没能找到帮手,只能跟妻子没白没黑地摘,“一是怕最近的连阴天影响棉花质量,二是担心棉花被盗。”朱兴亮说,以往棉花不值钱,个别人摘点回去填被是无所谓的事情,可现在一小捧棉花就是几十块钱,让人摘去损失可不小,因此防盗也成了一件大事。
现在,朱兴亮家里还存着4000斤棉花,“我们家家都存棉花,今年存往年也存。”朱兴亮说,因为10月11月是集中售棉的时期,所以卖不上去价格,再者来年一二月份卖棉花,也是为了凑钱过好年,这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习俗,年年如此。至于今年棉花涨价,朱兴亮认为,不是存棉的习俗造成的,“今年我们肯定早卖,拖到明年怕价格跌下去。”
#p#副标题#e#
■第三站:高青县棉花办公室 产业调整棉花越来越少高青县棉花办公室副主任韩凤云也认为,棉农惜售即便存在也不是导致棉花涨价的主要原因,“今年棉花确实减产了,但并没有绝产,减产幅度也就是两成左右,棉花价格的涨幅可比减产的幅度大多了。”韩凤云告诉记者,棉花之所以涨价,从根本上说,还是因为农村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。
拿高青县来说,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,种棉面积还保持在三十二三万亩,进入本世纪就锐减至26万亩,而近几年萎缩的态势更加明显,现在的种植规模已经减到了八九万亩的程度,而这一切都归因于棉农更会“算账”了。高青所处的鲁北地区之所以成为棉产区,是因为当地盐碱化严重,经济作物无法种植,粮食亩产量低,种植棉花是“性价比”最高的选择。可现在农村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,农民就业机会增加,种粮之风越来越盛。对此,韩凤云解释说,种棉花离不开人,为防虫子三两天就要喷一遍农药,还要掐枝、摘桃等多道手续,无法让农民从田间地头脱身。而转种小麦、玉米之后,虽然单亩经济效益下降很多,但因为不需要“贴身看护”,劳动力就解放了出来,到附近工厂打打工,赚的反而比种棉花多。
淄博市桓台县就是个活例子,早些年这里的棉花种植面积在整个鲁北都能排上号,可随着该县大力发展厨具生产,进而成为“中国厨都”,县里的棉花产量就一降再降,现在已经基本全部换种了小麦和玉米。
■第四站:滨州市邹平县 “新疆棉”何时现身救市?
本来纺织厂落户棉产区,看重的就是当地的棉花资源,可随着纺织厂越做越大,当地棉花资源却逐渐枯竭。这个看似悖论的现象,就活生生地发生在滨州市邹平县,在这里有规模亚洲第一的纺织集团——魏桥创业集团。
青岛有个海尔路,邹平有条魏纺路,沿着魏纺路一路驶来,记者看到的是一片片小麦和玉米。“这些地方以前种的都是棉花,魏棉(魏桥创业集团的简称)搬过来以后就逐渐没有了。”当地出租车司机刘先生告诉记者,魏棉最初不在邹平县,搬到邹平就是看中当地的产棉优势。建厂以后,当地老百姓的确是富了,邹平县也有了很大改观,可随着魏棉的规模从一个厂区扩大到五六个,种棉花的越来越少,“光魏棉一个集团就能消化10万以上的劳动力,谁还有心思种棉花啊。”刘先生说,邹平从产棉大县变成无棉县。
“往年这个时候,全是新疆的棉花车,今年大部分是河北和省内的。”在魏桥集团第一生产区对面,一位老人告诉记者,往年到了棉花收获的季节,这里会出现一些挂着新疆牌照的大货车,今年到现在还没有见到。
什么是“新疆棉”?在当下的购销形势下,“新疆棉”被很多人当做了“救市主”。新疆因为特殊的自然环境,非常适合棉花种植,近几年棉花产量已经占到了全国的40%左右。而且今年“新疆棉”碰上了丰年,预计地方种植的1420万亩棉花,总产可达150万吨。可想而知,一旦“新疆棉”全面投放市场,对于棉花价格的拉动效应可谓是惊天动地,而对目前身处“千年极寒”的纺织行业,更是一股100度的热流。然而,在记者的多日走访中,却始终未见质优价廉的“新疆棉”,这成为记者心中最大的问号。
“主要是运力不够,新疆有棉花运不出来。”正一家纺厂的王先生告诉记者,这是因为棉花“打不过”水果。10月11月,正是新疆水果集中上市的时期,火车、货车等大批运力都投入水果运输,而相对容易保存的棉花只能等过了水果运输的旺季再投入市场,“往年都是这个样,‘新疆棉’都会比其他地区的棉花晚上市。”
然而,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。“现在新疆的棉花也不便宜,籽棉收购价也涨到5块多钱了,估计很快就到6块钱了。”高青县流云纺织厂的业务员孙先生告诉记者,他去新疆跑棉花的时候发现,前来收棉花的各地厂家不少,真正带着棉花回去的不算多,当地的棉花几乎都“有主”,有的还没采摘下来就已被预订了,“人家说,这是期货!”
凡本网注明“来源:XXX”的作品,均转载自其它媒体,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,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。
如因作品内容、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,请在相关作品刊发之日起30日内进行。联系方式:400-700-0065
在摘编网上稿件时,由于网络的特殊性无法及时确认稿件作者并与作者取得联系。为了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,及时准确地向权利人支付作品使用费,请作品著作权人及时与本网站联系,以便支付稿酬。